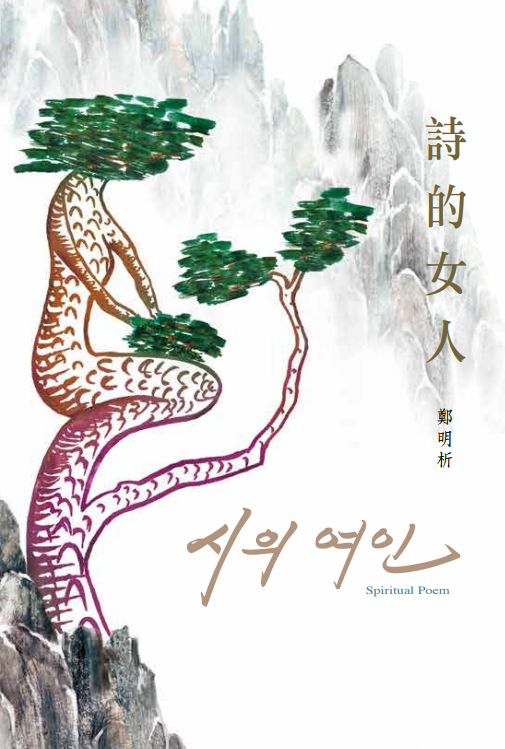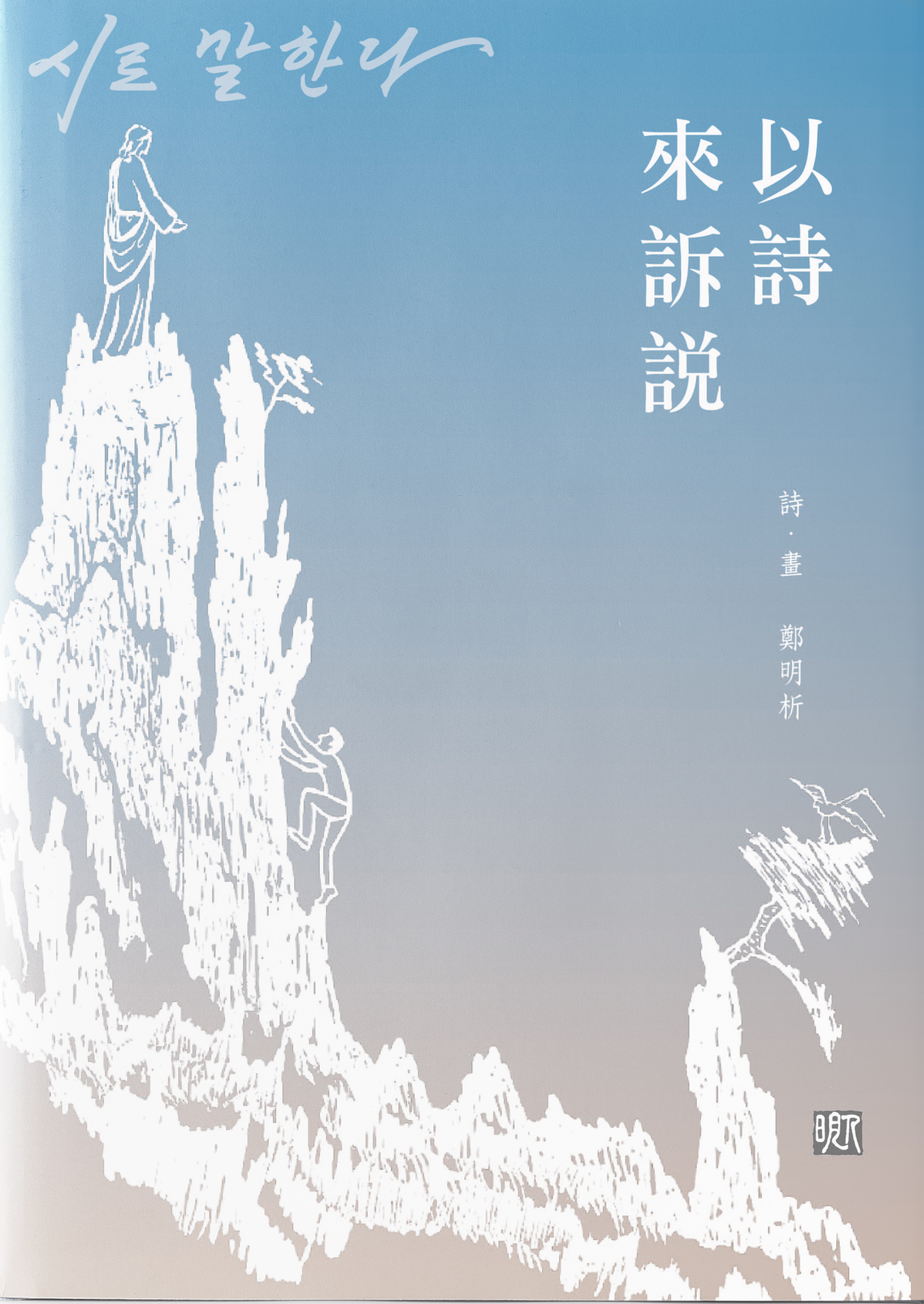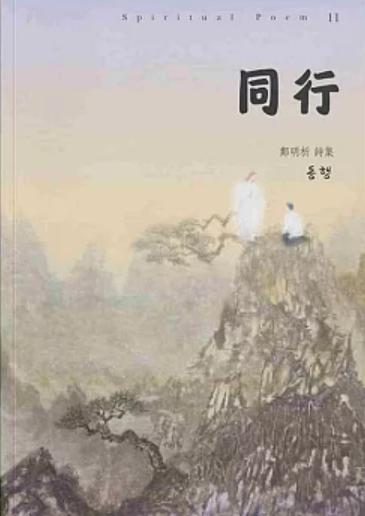〈從信仰詩句找回生命意義?淺析鄭明析先生的詩文〉
蔡安迪

文學研究者大多都能理解,在西方文學悠久的傳統中,基督信仰自古至今都有著深刻的影響。[1]正如學者楊慧林所言,哲人所傾心的「詩性道說」與詩人所神往的「靈性憑附」是不斷地在發生交互作用的。[2]詩,有極高的能力,可以將神聖和藝術完美地結合。詩人們則不斷嘗試「呈現無法呈現的東西」;這些被遺忘的「詩性智慧」,有助於讓我們覺察到自我的「有限」,邁向「超越」的可能。[3]
德國19世紀神學家及哲學家,被稱為現代神學、現代詮釋之父的施萊爾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是一位開啟西方近代浪漫主義思潮的大師。他在他那個深受啟蒙運動思想影響而有反宗教情緒的時代,希望能對當時知識份子輕視宗教的狀況做出澄清,並且重新定義宗教,因此施萊爾馬赫在他的著名大作《論宗教》一書中強調「宗教的本質既非思維也非行動,而是直觀和情感」[4]、「實踐是技藝,思辯是科學,宗教是對無限的感覺和鑑賞」[5],因此他說「對宇宙的直觀,就是宗教最普遍的和最高的公式」。[6]此外,施萊爾馬赫認為,詩、音樂最能表現宗教,而不是那些太過理性的哲學和科學知識。他認為這個世界上存在著一些有使命的人,由於自身擁有對宗教絕對的敬虔,因此能夠以強大的感知和表達,向世人傳遞一種對絕對者的仰望:
他向那些人描述天國和永恆,作為一個欣賞的和統一的對象,作為你們的詩歌所仰望的東西的唯一不竭的源泉。所以,他力求喚醒還在昏睡中的更好人性的萌芽,點燃對至高無上者的愛火,讓平庸的生命變成崇高的生命,讓大地之子與他們同屬的上天和好,使這個時代對粗鄙物質的依賴性保持一種抗力。[7]
以上可見在西方文學傳統中,基督信仰是如何與詩詞歌賦交織出最燦爛美麗的話語,澆灌著整個文化土壤,讓人們找到生命的可貴和光輝。
帶領西方近現代文明的宗教改革家們,也以基督信仰的精神創作了不少感人的詩句。在路德之前,教會的讚美詩歌皆用拉丁文寫成,路德卻以基督徒整體應該要平等的觀念,把許多難懂的拉丁文詩歌翻譯成德文,讓教會全體都能一同敬拜唱詩,期待使神的話語能藉着詩歌活在人們心中。此外,他也將他宗教改革「這是我的立場!」的信仰精神融入在詩句裡,留下不少膾炙人口的經典名句。另外的宗教改革家,18世紀衛理宗的創始人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的弟弟查理•衛斯理(Charles Wesley,1707-1788),也以創作大量聖詩著稱。查理斯一生中都規律地寫詩,總數估計有七千三百首,甚至因為他在詩歌方面的成就太卓越,而使後世幾乎忘記了他作為傳道牧者的身分。
同時是一位多產而大量創作的詩人,身為東亞新興教會的創教領袖,鄭明析先生誕生於二戰結束的1945年,然而和平並未馬上到來,故鄉韓國立刻又發生了韓戰,而使他的童年陷入另一場恐懼和飢荒的陰影中。鄭明析先生的人生道路由此出發,在韓戰後貧瘠的鄉村生活的不易和苦痛中,不斷嘗試藉由基督信仰尋找一絲希望的可能。
特別,鄭明析先生在青年時代因服役而直接親身參與越南戰爭兩次。身為一個底層士兵,他無奈所有平民百姓被戰爭之框無情地奴役,於是他開始藉由文字,特別是詩句的書寫,對戰爭發出了最無奈的痛心和抗議,也表達對年輕生命逝去的淚水和悲情嘆息。這是鄭明析先生作為詩人的起點。
站在底層平民的立場,鄭明析先生除了在詩句中藉由記錄戰場的各種悲情,也對引發戰爭的上位者和所謂戰爭英雄提出尖銳的批評。他的詩句反省並批判戰爭中各種荒謬和二元對立、敵我之分的錯誤框架。反戰與對和平的渴望,正是他寫詩的起點:
戰爭你這傢伙
我不會對敵人開槍
但唯獨你
我必要置你於死地
在你死亡
踏入墳墓的那天
和平的世界
才會真正來臨
愛與喜悅的理想世界
才會真正來臨
戰爭,你這混帳
因為你
連我純真善良的語氣
最近都變得粗魯許多!
戰爭,你這怪物
因為你
我來到這陌生的土地
在叢林中
吃盡各種苦頭
啊,戰爭
因為你
這世界
化為慘不忍睹的血海
戰爭
你讓年輕人的胸口
爬滿了蛆
神會與我一同
在這地球村上
實現愛與和平的世界
必定會速速
將戰爭你逐出去
扔進地獄火海……。[8]
因為嘗試反戰相關的文學創作,讓鄭明析先生養成了寫詩的習慣。之後在1995年,鄭明析先生其他多樣化的作品開始刊登在韓國的《文藝思潮》月刊,也算是他正式以詩人的身分步入文壇。之後鄭明析先生陸續發表了暢銷詩集《靈感的詩》1-4集,這當中至少有十首詩榮登總括韓國百年詩史的《韓國詩大事典》(2011)。
正如史懷哲曾嘗試探尋歷史上的耶穌,[9]基督信仰也以各種不同於傳統的樣貌出現在各地。耶魯大學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1923-2006)教授也將耶穌形象的變遷置於文化史脈絡,反省歷史上的耶穌形象「最為明顯的特徵不是同一性,而是萬花筒般的多樣性」。[10]鄭明析先生的詩句中,也訴說自己如何在面對困苦生命歷程的同時,將耶穌基督詮釋為信仰者屬靈上的新郎,而寫下信仰之愛的美麗篇章:
服事
因凜冽的風
身體削磨
內心也削磨
烏黑頭髮
已成白雪紛飛
我如此經歷風雨
服事良人如待己身
願良人乘坐
我手親造的扁舟
沿著水鳥哭泣的江岸
划槳向前
直到走盡我的餘生
直到良人內心喜悅
譜寫詩歌新曲調
至歲月磨盡
都為他吟唱。[11]
即便經歷各種因為堅持信仰的獨立精神而經歷的宗教逼迫,即便年華老去、青春不在,鄭明析先生持續以詩句將基督詮釋為自己的新郎,細膩地用文字刻畫信仰之愛為一種精神上、靈魂上的戀愛。於是,這份將聖子耶穌作為新郎的愛,變成了鄭明析先生一生中克服各種困境的根本動力。
此外,在鄭明析先生的詩句中,鄭明析先生和家人之間真摯的情感,父母親情的點滴故事也充分展現:
某處傳來
神的聲音
我也與你
去了又回
你身為人
看不見我
渾然不知
我在身旁
與你同行
只因你我
太過靠近
離開故鄉
時隔已久
再次返鄉
如在夢境
想要先訪
父親之墳
於是前往
他的墳上
請安問候
即使叩門
也無聲息
即使呼喚
也無聲響
開啟墓門
只見空房
心中感嘆
時候到了
父親已去
天上國度
我的父親
離去已久
以致房內
蛛網深結
我獨坐在
墓室之中
回憶昔日
淚流成河
縱使你有
千里之眼
又有何用
父母與你
太過靠近
反而讓你
無法看見
更何況是
屬天父母
與你更近
你又怎能
得以看見
母親流淚
緊擁相迎
那是母愛
哺育之情
母親育我
恩情浩瀚
愛子心切
觸動上天。[12]
此外,古典的韓國文化中本來就有著一份對真理和是非對錯的執著,這在號稱朝鮮儒者忠誠典範的鄭夢周(정몽주,1337-1392)「向主一片丹心」的著名詩句中表露無遺。時代變遷,這種忠誠和敬虔在鄭明析先生詩句裡也依然存在,只是以基督信仰的形式表達著:
一片丹心
暴風雨
襲擊而來
暴風雪
狂亂紛飛
豈因歲月流逝
山嶽化為江水流淌
江水化為山嶽聳立
患難風暴
縱然襲擊
那內心
一如往昔
那模樣
一如往昔。[13]
幸福仍會前往
風雪大作的人生寒冬之中
幸福仍會前往
患難痛苦
椎心刺骨的生活中
我的希望
仍會達成
在那荊棘路上
幸福仍會前往
幸福
不願隨意迎向任何人
於是與風雪同行
邁向奮鬥掙扎的
痛苦道路
希望
也不願隨意與任何人生活
唯獨前往拜訪
忍耐堅持的人。[14]
鄭明析先生的信仰詩句,讓我們看見他即便身處20世紀人類文明劇烈變化中,對於追求真理的嚮往卻從未動搖。他對於幸福、希望的重新定義,也為我們打造出一塊能夠追求「精神獨立、思想自由」的「第三空間」[15]的心靈高度。
時間越到現代,有學者認為,上個世紀西方文學最普遍的主題,是表現出一切都無意義,並且宣洩由此而生的厭倦、失望和孤獨的情緒,呈現出一個以「否定」換取「超越」的時代。[16]人們似乎都在後現代的懷疑和虛空的迷霧中感到茫然,而不知何去何從。是否正如部分學者所建議的,也許某些植根於「有限性與超越限度的他者」之間的神學語言,有助於讓我們走出「意義」消解的困苦。[17]身處西方另一隅的東亞,鄭明析先生的詩句,是否就代表著一種努力,讓我們在基督信仰和文學結合之中找尋到存在意義的可能?
20世紀東亞的主流論述是個「史詩」時代,國家分裂、群眾掛帥,革命聖戰的呼聲甚囂塵上。然而,如同王德威院士所提問的,是否時代中還存在有少數有心人反其道而行,以創作呼喚著「抒情傳統」,[18]彰顯政治變局之外更深刻的價值呢?鄭明析先生的動人詩句也許就巧妙地呼應了那個屬於古典的抒情傳統。
最後,學者也曾探討,沒有身處「邊緣處境」的親身經歷,不曾遭遇虛無和陷於絕望,任何形式的宗教歸信都是不真實的。而且宗教歸信也不可被簡化為一個普通的倫理問題,反而是一個對普通倫理的超越問題。因為若不超越「倫理的人」(Homo Ethicus)便無法建立起與神聖者的面對面的關係,從而真正成為一個「宗教的人」(Homo Religiosus)。[19]身為學術讀者也罷,或者信仰者的視野出發,我們藉由鄭明析先生的深刻生命話語,特別是他身處被世人視為異端、邪教教主,受到各種無情批判、踐踏之際,依然在細膩的詩詞語句裡,讓基督信仰發出愛的光亮,可以說就是一種「宗教的人」(Homo Religiosus)的超越性典範。鄭明析先生詩句中的「獨立信仰之追求」和「深刻抒情的筆觸和呼喚」,也許就有可能成為我們的當代文化裡,所遺漏缺少的那份充滿人格魅力,還有熱情的、深切的、美的宗教情感。[20]也像是施萊爾馬赫所言,鄭明析先生的詩句喚醒還在昏睡中的美好人性,也點燃我們對信仰的追求動力,讓平庸的生命,能有機會保持對物質和庸俗的一種抗力。也讓我們看到即便在所謂的後現代社會,基督信仰在文學中依然充滿活力,為世界帶來更新的力量。也如姜台芬教授所言,聖經影響下的文學,持續從另類的、非傳統角度,提示新時代問題的癥結。
[1]詳見姜台芬,〈聖經與西方文學——代序〉,《聖經的文學迴響》(臺北:臺灣大學出版社,2012)。或見姜台芬,《創世記精意新探》(臺北:臺灣大學出版社,2012)。或見劉建軍,《基督教文化與西方文學傳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1-14。
[2]楊慧林,〈“詩性”的詮釋與“靈性”詮釋〉,《長江學術》2006年01期,頁126。
[3]楊慧林,〈“詩性”的詮釋與“靈性”詮釋〉,《長江學術》2006年01期,頁128。
[4]施萊爾馬赫著;鄧安慶譯,《論宗教》(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頁29。
[5]施萊爾馬赫著;鄧安慶譯,《論宗教》(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頁30。
[6]施萊爾馬赫著;鄧安慶譯,《論宗教》(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頁32。
[7]施萊爾馬赫著;鄧安慶譯,《論宗教》(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頁8。
[8]鄭明析,《戰爭是殘忍的。愛與和平》(第二冊),頁151-153。
[9]Albert Schweitzer, The quest of the historical Jesus : a critical study of its progress from Reimarus to Wrede, (London: Suzeteo Enterprises, 2011),pp3-5.
[10]〔美〕帕利坎(J. Pelikan)著;楊德友譯,《歷代耶穌形象》(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5),頁5。
[11]鄭明析,〈服事〉。
[12]鄭明析,〈孝順〉。
[13]鄭明析,〈一片丹心〉。
[14]鄭明析,〈幸福仍會前往〉。
[15]王德威曾研究劉再復的文學精神:『當年陳寅恪悼王國維的名言,「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貫串字裡行間。劉再復則更提出追求精神獨立、思想自由,就必須打造「第三空間」。……他甚至不認為自由便是西方哲學家所說的「自由意志」,也與當代自由主義大相徑庭。 「自由乃是一種『覺悟』,乃是一種在嚴酷限制的條件下守持思想的獨立和思想的主權, 並在種種現實的限制下,進行天馬行空似的的精神價值創造。」 正因為有此覺醒,他提出「第三空間」。相對於祖國與海外所代表的第一和第二空間,「第三空間」看似虛無縹緲,卻是知識分子安身立命之處。 ……』詳見王德威,〈山頂獨立,海底自行〉:https://www.linking.vision/?p=5283。
[16]楊慧林,〈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的神學傾向〉,《四川外語學院學報》1993年04期,頁9。
[17]楊慧林,〈當代神學對文論研究的潛在價值〉,《文藝研究》2004年03期,頁42。
[18]詳見王德威,〈山頂獨立,海底自行〉:https://www.linking.vision/?p=5283。
[19]段德智,〈試論宗教對話的層次性、基本仲介與普遍模式:三論21世紀基督宗教的對話形態〉,《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55卷第4期(武漢,2002),頁426。
[20]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的陳獨秀在尚未完全成為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前,曾經反省過東方文化,認為在「文化源泉里,缺少美的、宗教的純情感,是我們不能否認的。」、「文化源泉里缺少情感,至少總是一個重大的原因。現在要補救這個缺點,似乎應當拿美與宗教來利導我們的情感。」、因此陳獨秀當年曾經主張過,要把「耶穌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培養在我們的血里」詳見陳獨秀,〈基督教與中國人〉一文。